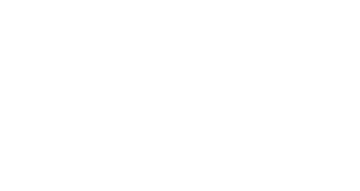這碗飯,走味了
10/19/2009 瀏覽:724
這碗飯,走味了 這個世界變得太快,每個變化都牽動著我們手上捧的飯碗。 老師、醫生、記者、電子新貴、銀行行員、土木工程師、國會助理, 這些過去人人稱羨、足以安身立命的好工作,為何竟成了苦差? 曾月入百萬元的婦產科醫生如今月入6萬元; 科技新貴想轉業去賣香雞排; 老師得擔心被家長威脅恐嚇; 銀行行員流落街頭推銷現金卡; 記者成了人人喊打的狗仔; 土木工程師得昧著職業道德幫政策背書; 政治幕僚成天聽選民訐譙… 走味的飯如何嚥下去? 靠什麼信念繼續堅持? 且聽他們娓娓道來。 老師只能求自保 許淑屏,三十二歲任職國中國文老師十年 十年前,一些成語、典故,一個班至少兩三個人知道。 但現在很簡單的,像「桃李滿天下」就沒人聽過。 學生亂用成語也是常態,他們會說:「這家餐廳生意盎然。」 最可怕的是作文,像我最近改到一篇,題目是:「當我失意的時候」, 有同學寫:「當我失意時,會請媽媽拿我的照片給我看,讓我回想我是誰。」 改完我虛脫無力,只能把這些「趣事」說給同事聽,調劑心情。 我當學生時,老師是權威、高高在上的, 像我的國中老師,一個眼神掃過來,我就全身緊繃。 以往升學掛帥下的過度體罰、侮罵,會在孩子心裡留下創傷。 但那時的家長相信嚴師出高徒,他們相信老師做的一切都是為孩子好。 現在不一樣了,我受的訓練,是要和學生當朋友、打成一片。 矛盾的是,家長卻不再相信 「老師的出發點是為孩子好」這件事, 整個社會用很嚴厲的眼光評斷老師,卻沒有給予相對的尊敬。 有一次,二個同學打架,細問後,我發現二人都有錯。 學生回家卻說了另一套版本,家長直接帶孩子去醫院, 拿著驗傷單來質問我: 「老師,我在教育局有朋友,妳要還我兒子公道。」 也有些家長會不經意透露:「我認識某立委、某媒體。」 言下之意,就是「老師,妳小心點。」 這種話聽多了,單純的校園,竟有種人人自危的不安。 如果動輒得咎,也只能明哲保身, 現在只要和學生身體有關的事, 我第一時間就請家長來學校, 坦白講,處理小事都得大費周章,我是保護自己。 大環境讓人漠然,只能從教學找回熱情。 我花很多時間改週記和日記,和學生對話。 曾有個學生上大學後回來看我, 謝謝我當初認真回應他的週記,讓他覺得被在乎。 只要還有這樣的學生,我就覺得當老師是值得的,還可以堅持下去。 賣冰比當醫生好 周遵善,46歲北醫婦產科醫師、美塑治療研究學會理事長 十三年前是婦產科的黃金期,每年新生兒四十二萬人, 我的診所一個月賺一百萬元,在業界算少了。 那時我手拿鴨嘴鉗,意氣風發,萬萬沒想到, 今天的我會拿著玻尿酸針,在病患臉上注射。 婦產科診所開了三年,我歇業出國進修。 回國後,世界就變了,可怕的不是出生率下降,而是健保。 我在大醫院婦產科任職,現在醫生沒有底薪,採業績制, 看一個病人抽一百四十元,你猜我一個月領多少, 不要懷疑,六萬元。 健保的餅就這麼大,吃的人太多。 我一九八八年畢業時,台灣有六所醫學院,一年生產四百個醫生, 現在九所,一年生產一千三百五十個醫生。 僧愈多粥愈少,大家都吃不飽,甚至餓死。 為了生存,婦產科門診我照看,同時進修美容醫學, 最近還開了醫生在職進修班,幫轉型的醫生補習。 一百多個學員,婦產科醫生就占三成。 台灣的美容學會、抗衰老協會,都是婦產科醫生當理事長, 原先看下半身的,都來兼職看上半身,都只想求個生路。 最讓我難過的是,醫院變成商店、醫生成了業務員。 我在婦產科,拉開抽屜,一堆自費的好藥、好器材, 面對病人時,「我有更好的鴨嘴鉗,但得自費,妳要不要?」 這種話我說不出口。 現在碰到想考醫學院的年輕人, 我都會勸,你對生命科學有興趣,當醫生很好, 如果是為了社會地位、賺大錢,這是錯誤期望, 賣剉冰都比當醫生好。 新聞只做給長官看 丁文怡(化名), 33歲從事電視台記者8年前陣子在外頭採訪, 一對父子經過,小孩指著我手上的麥克風問:那是什麼? 爸爸回他:那是狗仔,不要理他們。 我念新聞系,實習時就確定要當記者,很嚮往能在第一線流汗採訪。 8年前初入行,接到我名片的人,都說: 「哇,記者啊,很棒耶。」 但現在,沒吐口水算客氣了。 記者這行之所以有尊嚴,是因為對社會有幫助,現在卻成了社會亂源。 現在的新聞不是做給觀眾看,而是給長官看。 過去我跑科技、醫療,報導對癌症病患有用的資訊, 但現在長官會說,這些別台做就好, 他寧可要「某校的學生長得很像某藝人」的爛新聞,只因為是獨家。 長官叫我們跟著報紙跑,即便查證後,發現報紙的資料是錯的, 長官還是信報紙上寫的。 主播也不管我訪到什麼,照著報紙念稿頭。 認真的記者被獨家的壓力逼瘋,想省事的就做假, 路上拍一個人的背影,就說對方是皮條客。 有一次長官叫我拿針孔去拍一個小吃攤,叫我硬扣對方衛生不合格。 我很生氣的反抗 :「沒有衛生局檢驗,你有沒有想過會毀了別人的生計?」 但我還是做了,第2天把帶子連同辭呈交給長官。 也有人衝著這行光鮮亮麗、能認識明星名人, 擠破頭進來後,才發現自己只是穿套裝的廉價女工, 算算時薪才一百出頭,比7-11還少。 到現在,我已換了4家媒體,很多人說:「妳可以選擇不要做。」 但我相信,比起其他職業,記者比較有可能改變這個社會, 一則好新聞是能幫助人的。 我的底線是絕不做假,如果哪一天守不住, 也是我完全夢碎、離開的時候了。 科技新貴變碗粿 大勝(化名),三十一歲從事 DRAM 設備工程師五年 我五年前野心勃勃進入半導體業, 那時最基層的工程師都領一百多萬元股票, 心想:「明年就輪我了。」 誰知道那是最後一年榮景。 接下來的三年,沒獎金、沒加班費, 每年只有七十萬元年薪。 跟我同梯的工程師因為沒撈到錢,陸續走了。 但我不甘心,熬了快四年,心想說不定以後有好康的。 我的工作是保養維修機台,其實跟修車工人沒兩樣, 只不過我穿無塵衣、戴手套,二十四小時輪班。 公司配一支手機隨時遙控我,半夜被call回公司修理機台是常有的事。 我月薪快六萬元,算起來比很多行業好了, 但如果除以每天十幾個工時,真沒好到哪裡去。 以前的科技新貴賺得多,四十歲退休的一大票, 現在沒人敢如此奢望了。 我身邊的工程師,每個都說想去賣香雞排,但有勇氣轉業的沒幾個。 我表弟研究所剛畢業,說要來半導體業,我勸他別來。 像我待了五年,會的就這些,已經沒地方可去了。 未來的競爭力在哪?是我最大的焦慮。 去年公司營運轉好,我領到五十多萬元獎金, 但並沒特別開心,因為明年會怎樣,誰也不知道。 為了當科技新貴,我捨棄好多, 從前我熱愛拍照、打棒球,如今只剩上下班、等電話。 最近我開始進修、主動爭取公司其他部門的業務, 讓自己朝管理階層發展。 希望三十五歲可以找到一份準時回家、下班後不用接電話的工作, 夢想雖然越來越小,但這樣就夠了。 銀行行員金飯碗褪色 周家友(化名),三十歲擔任銀行行員七年大學畢業後, 我在雜誌社工作,日夜顛倒、週六日加班。 我一直羨慕在銀行工作的家人,他們捧著金飯碗, 過著朝九晚五的安穩生活。 我發現某銀行招考行員,想也沒想, 便向朋友借書猛 K 二個月,沒想到考上了。 我猜我運氣好,因為很多人補習都上不了。 受訓後,我被派到分行,一切如我所想, 坐櫃台、吹冷氣、數鈔票,三點半鐵門拉下來,五點就下班。 但這樣的美好,只維持二個月。 有天,主管突然下令,全部行員都要出去推銷現金卡。 原來,我正好撞上七年前現金卡的戰國時代, 各家銀行猛下廣告、浮濫發卡的惡性競爭期。 之前朋友都不相信我考上銀行,說我一定是去當業務, 我還嗆聲說:我是正規行員。 當我夜市、辦公大樓前擺攤,拿著傳單和贈品追著路人跑時, 我也無法相信,我的銀行夢竟然淪落街頭。 有些同事受不了,都辭職了。 一個月最少要發一百三十張卡,我把親朋好友拉來衝業績, 警告他們辦好就解約。 現金卡只要發卡,不管有沒有使用, 這筆金額就算在借貸額度裡,很多人都不知道這陷阱。 路上拉到的客人,我卻只說,這是預備金, 想用就用,不用也不會壞。 發出一萬張卡後,另一個惡夢來了,我被調到催收中心。 戴著耳機坐在電腦前面,一天打二、三百通電話催帳, 不是被罵,就是聽到一個個無奈父母為兒女還債的故事。 我還在電腦檔案裡看到自己的簽名,我以前發出去的卡, 現在由我自己催收,只好努力替對方擬定還款計畫,希望能幫他一把。 從放款到討債,雖然和我的銀行夢差距太大, 卻讓我看見社會上形色的人。 我以前很難相信開賓士的人,其實負債累累。 原來當美夢褪色,我才看見真實的人生。 找不到工地的土木工程師 洪德,四十五歲從事土木工程師十七年 我求學時期,前三志願是醫學、電機、土木系, 當時家人要我捨醫科念土木。 一九八九年台大畢業後,很多重大建設起飛, 我順利進入工程公司,被派到南迴鐵路當監工。 此後數個月,每天十二小時,我都待在暗無天日的隧道裡。 第二個工地是地下室,有次不小心卡進一個四公尺深的洞,差點沒命。 當時雖辛苦,但案子多得接不完,我一路從工地主任升到總工程師, 覺得前途充滿光明。 沒想到九二一大地震後,很多建商都倒了, 我在一家公司做研發部副理,但公司縮編, 我竟被下放到工地當監工。 很無奈,快四十了,想離職但外面沒工作,只能等著被資遣。 那時我到一棟大樓勘災,地上二樓變成地下一樓, 看得我頭皮發麻,明顯偷工減料。 我的工作若少了職業道德,危害的是人命, 然而我們的職業道德卻被挑戰。 雪山隧道來說,明明提前通車有風險, 但政策說通就得通,毫不尊重工程師的專業判斷。 台灣重大建設已經不多了,營造廠又不具國際競爭力。 日本、韓國的廠商有國家培植,可以來台灣接案子, 像捷運的潛盾工程都是外商在包,台灣看不到土木工程的前景。 如今我經營一間小事務所,員工不多, 但至少不用擔心被資遣或違背理念。 早知道,當初就該選醫科。 國會助理寫作秀劇本 Sandy(化名),37歲 任職國會助理10年前幾天,老闆又把我臭罵一頓, 說他很久沒上媒體了! 我心想,你立委的正事不做,乾脆進軍演藝圈算了。 氣歸氣,我早也麻木了。 十幾年前念大學時,經濟起飛, 可是很多環保、人權、勞工法令來不及接軌, 透過立法最快,所以我滿懷理想進了立法院。 早期的在野黨還算認真,抓政策缺失、補法律不足。 我要幫立委收集資料、擬質詢稿、研究法案、看預算書, 每當我間接促成好法案通過,那是很有成就感的。 但政黨輪替後,民進黨忽然擁有好大權力,開始貪污腐化; 而國民黨立委大都透過地方勢力、家族派系上來,完全不懂監督。 如今,該審的法案、預算不審,大家最喜歡安排首長報告, 因為立委可以在媒體上開砲。 立委還要忙著做選民服務: 跑紅白帖、關說工程、幫朋友解決司法糾紛。 我最主要的工作也變成設計一些譁眾取寵的噱頭,讓老闆上媒體。 最近朝野嚴重對峙,我還有接不完的電話, 聽瘋狂選民打來罵三字經,好像另一個《2100全民開講》。 太靠近政治,人會失去夢想。 我已經好幾年不參加遊行,都假的,何必幫忙背書? 去年有個助理才來1年就買了BMW,聽說是拿回扣賺的, 老實說,我輕蔑他的操守,又羨慕他膽敢這麼幹。 10年來,我做過藍、綠、橘的立委助理, 但以後的菜鳥立委怕我比他還懂,不一定敢再請我, 所以此地不宜久留。
本平台由情報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維護建置
Copyright © 2002-2025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 2002-2025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