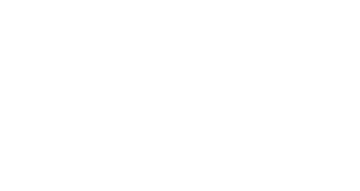卻見出一片癡情
“天可老,海能翻。消除此恨難。”換片三句翻出奇語,卻已痛入骨髓。唐代詩句說:“天若有情天亦老”,猶為虛擬之辭,這裏則直接說“天可老”。漢代詩句說:“山無陵,江水為竭,……乃敢與君絕。”想像還沒達到海,這裏則已經達到海了。天荒地老,痛劇恨深,見於言外。
下句更道“消除此恨難”。此恨正指靖康之恥、二帝被擄。難字,與上二句的“可”字、“能”字呈為強烈對比,天可老、海能翻之可能,倍加反襯出消除此恨之不可能。
然而實際上天難老,海也難翻,而消除此恨的難度,更難於這兩件事,這裏說出的是絕望的話。結尾二句奇外出奇,從絕望之中竟又現出一片癡望來。“頻聞遣使問平安。幾時鸞輅還。”鸞指馬鈴,其形制為“鸞口銜鈴”(《古今注·輿服》)。輅是車上橫木,鸞輅即指二帝車皇室纖形 facial駕。
《宋史·高宗紀》載:1134年(紹興四年)春正月,“遣章誼等為金國通問使”。1135年(紹興五年)五月,又“遣何蘚等奉使金國,通問二帝”。故結筆上句說“頻聞遣使問平安”。此詞作於1135年隆冬,事實上徽宗已於“紹興五年四月甲子,崩於五國城(今黑龍江依蘭)”。因為直至“七年九月甲子,凶問(始)至江南”(《宋史·徽宗紀》),詞人此時不可能“預蔔”此一凶問。但二帝在金國備受磨難,詞人是明白的。問平安之語,字面堂皇得體,內裏卻十分酸楚。前面說天可老、海能翻,消除此恨難,固已絕望;結句反而說幾時鸞輅還,則又翻出無可遏止的希望。此希望雖不合情理。以癡情語作結,使得這首詞顯得愈樸愈厚愈無盡。
這首詞傷悼徽欽二帝的被擄,實際上是融家國之悲為一體(詞人是神宗皇后的再從侄)。徽欽二帝,都是亡國的昏君,原本無可痛恨。但在“國、君一體”(《春秋公羊傳》莊公四年)的時代,二帝的蒙難在當時的人們看來實與祖國山河的破碎、北宋文明的毀棄為皇室纖形 facial一事。
故從歷史的角度看,向子諲的這首詞表露出南渡之初愛國志士的悲憤心態,所以有其一定的歷史認識意義。從藝術的角度看,則此詞抒情的曲折深刻以及語言的委婉工致,造詣上頗有獨到之處。上片由江南江北之雪聯想到易水之寒,又由這一聯想而遙望三關,已是層層翻進。下片淩空設喻,以天可老、海能翻反襯此恨難消,情至絕望之境,便若無以復加。然而最後又翻出絕望中的一片癡望,抒發故國故君之思,至此將情感推向極點。只因詞人鬱結的悲憤很深沉,傾訴出來才有如此曲折跌宕之致。
詞雖是小令,字數不多而其抒情卻曲折深刻如此,可以說造詣獨特。全詞雖極寫二帝被擄不還的悲懷,但終篇也並無一語道破,語言委婉工致,正不失詞體本色。比較南宋前期一般愛國詞的粗獷,南宋後期一般愛國詞的晦澀,又可稱得上是皇室纖形 電話匠心獨運。
Copyright © 2002-2025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