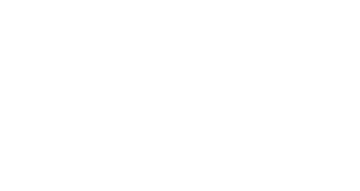憤怒和抓狂將理性拋到九霄雲外
初次見面,還是在十四年前。白音寶力格被父親送到了一位奶奶家,和一個叫做索米婭的姑娘就此相識,黑黑的眼睛透著精靈的光,一閃一閃的望著白音寶力格。白音一心專研機械和獸醫技術,少言寡語,喜歡思索。索米婭則在給鄰居家的羊群守夜。
小時候,索米婭的一切,在白音寶力格看來都是妙不可言的:某個春季,索米婭朝我跑來。天氣熱了,她脫去了臃腫的皮袍子,穿著一件奶奶穿舊的的薄皮袍。也許是青春期的緣故,索米婭的聲音聽起來永遠是甜的。“巴帕,你騎得不錯。”她像以前一樣,扳著我的肩頭,搖著我。
接著成年的日子就這樣來了,儘管沒有人正骨宣佈過它的開始。一個純淨、透明的世界和一個可怕的羞恥的心在更替著。白音寶力格油然而生出難以理解的興奮和萌動。當青春這粒種子從心田上破土而出之時,惶惑中的我們能理解它的多少含義呢。
白音寶力格真切的體會到,那個熟悉的小索米婭,小小的,胖乎乎的,如今分明是一個修長、健壯、曲線分明,在陽光下折射異彩的姑娘。對於草原上的女人呢,夢中依稀隱現出迎面而來的猛士少年,橫刀立馬,英氣逼人。青春的朝氣,就像點著火的油桶滾滾而來。奶奶對索米婭這樣說道:“索米婭,唉,如果你跨過伯勒根河到了對面,我會愁死的。不如你們結成夫妻,這樣,我的一個寶貝都不會失掉。”
我想,白音寶力格和索米婭被道出了心思,一定是既興奮而又羞答答地不肯承認。
不過,終究這一切的理所當然,被白音寶力格的學習之旅耽擱了,嚴格來說,應該是摧毀。臨走,索米婭被派去送別白音寶力格。車子迎著烈風向前行進著,也許是離別的疾苦和日日夜夜累計的熾烈情愫,倆人抱在一起,難捨難分,並且白音寶力格許諾,回來就結婚。
人這一輩子,承諾這東西,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承受得住。動力火車的《忠孝東路走九遍》歌詞中最為貼切:看著一份愛有頭無尾,你有什麼感覺?有人走的匆忙,有人愛的心碎,誰會在意擦肩而過的心碎。我想白音寶力格最能體會這句話的意義何在。
幾個月的牧業技術訓練結束,白音寶力格回到伯勒根草原的時候已是五月初,草皮泛青的季節了。遇上黃毛鬼希拉,的確不是回來後的好兆頭。至少,白音寶力格在一堆人興奮的宣佈不久就會和索米婭結婚後。希拉的醉熏和鄙夷,開始覺得有點噁心,而後就是有著復仇的衝動:“那可真是個漂亮的小乳牛,我希拉連帶那個牛犢子也送給你。”
我想,每個劇集都有一個類似黃毛鬼的角色,猝不及防之間,就撕碎了人們幻想中羅曼蒂克的必遊景點一切。生活即是如此,充滿無知無畏而又無果而終的變數,我們無須自信的為未來的一切,做簡單抽象的拼圖。盡最大的努力,做最壞的打算,也許應該這樣。
索米婭與五個月前多了一層陌生感,總是小心地、遲疑地盯著白音寶力格。當他撞開門,看見索米婭高高隆起的肚子時,第一次他選擇相信黃毛鬼希拉。原來,就在他出去接受牧業技術訓練的幾個月裡,黃毛鬼暴力的佔有了索米婭。白音寶力格也知道,周圍也有許多頭上有一撮黃毛的殘弱的孩子,也是希拉給予的“苦果”。而更令人驚訝的是,周圍的人對此已經習以為常。
白音寶力格自然是難以接受,勃然大怒,可怕的痙攣陣陣襲來。猛撲過去,抓住索米婭的衣領,拼命的搖撼著她,似乎要求索米婭再一次印證已經寫好的結局,甚至算是祈求,索米婭能夠滿腹委屈的向他傾訴。
意外的是,她倔強的愈發沉默。“鬆開”。索米婭卻尖叫出來,“孩子,我的孩子”。掙扎中,她狠狠地在白音寶力格的手腕上咬上一口,撞開後風一樣的跑了出去。
他預料之中的驚訝,頹然而生。此時此刻,卻浮現白髮蓬鬆的奶奶神色冷峻地注視著白音寶力格:怎麼了,白音寶力格,難道為了這件事也值得去殺人。知道索米婭能生養,也是件讓人放心的社交信貸率計算器事啊”。
第一次讀到此處,我開始為奶奶的麻木不仁和自我滿足,感到傷心。之前的所有冷暖人心的往事,被一句話瞬間吹破,毫無影蹤。而後,我再讀到此處,多了份理解:無意去要求行將就木,年近終跡的
白音寶力格一時沒有緩過來,自以為奶奶至少會振臂高呼:“去吧,孩子。這樣的人,不配活到明天。”除了震驚、不解,白音寶力格更多的是孤獨和無助,心力交瘁的把臉深深的埋在黑駿馬的鬢毛裡。
也許,正如文中所說,他還不算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草原孩子。他讀過書,接受過系統的科學訓練,眼界和書籍的薰陶讓他覺得自己與這裡的確有所不同。似乎看到了自我的另一種渴望,這種渴望在召喚著他,驅使著走向更純潔、更文明、更尊重人的美好,也更富有魅力的人生。
可這一臉竄的“文明啟示錄”,也只不過是白音寶力格的自我安慰罷了。他打心裡眼裡知道,他不能沒有索米婭,她的柔情似水,幾度讓其沉醉。兩小無猜的日子,怎能說忘就忘,索米婭就像清泉一樣浸泡著白音寶力格的每一寸心田。他開始走到棚裡,輕聲呼喚著索米婭,希望索米婭能朝他撲來,述說著愛與哀愁。
不過,在他腦海裡幻想的波瀾壯闊,現實中如一潭死水,沒有一絲痕跡。
當白音寶力格復仇黃毛鬼希拉,忍痛回來的時候,卻發現索米婭和奶奶正在輕鬆的討論中紅花絨縫製的嬰兒鞋。
滿滿的絕望和傷心,毫不留情的把白音寶力格撲倒在地,沒有餘力傷悲,愛情這東西就像難收的覆水。他決定離開了。多年後,農牧學院大學生白音寶力格又回到了伯勒根河岸的草原,此行唯一目的:再尋索米婭。
此時,索米婭已經是四個孩子的母親,日夜不休似得的勞作,為了一個月四十五塊的工資。在冰封千里的冬天,索米婭就是在這塊石頭上蹲著,用力鑿開堅冰,把一桶桶水汲進水缸,運到學校。白音寶力格長時間觀察著她的一舉一動,覺得自己似乎看見了她過去的日子,也看清了她未來還要繼續度過的生活。
他的丈夫是大車老闆達瓦倉。索米婭趕在月夜給奶奶送葬的晚上,黑夜裡,路不好,車壞了,抱在孩子躲在扯下苦。達瓦倉尋聲而來,把索米婭母子二人送回蒙古包,而後覺得越發可憐,就這樣達瓦倉又趕上車,開了張結婚證,第二次去了伯勒根河岸。
多年後的見面,索米婭對著他回憶:“白音寶力格,那時我猜不出你在哪裡,我只記得馬車一搖一晃地走在河水裡,車輪裡濺起冰涼的浪頭。不過,我知道你非常討厭我有這麼一個女兒”。白音寶力格對索米婭說,其實他很喜歡其其格這個小孩……”索米婭,似乎都沒有來得及換氣,一口氣綿綿不斷的說出了埋藏多年的心事,邊說邊小聲的抽泣。
白音寶力格想替她叉掉那些淚珠,可是不敢。我很理解,曾經一切的美好,已逝。再一步,估計克制不住的情愫也會粉身碎骨。如今,你我近在咫尺,卻又似天各一方。
過了見天,白音寶力格想見也見了,索米婭的生活,不好也不是太壞。告別了達瓦倉,其其格和孩子們。索米婭陪著他,慢慢走著。當他說了一聲:“再見吧,索米婭”。這時,卻聽她突然憾人肺腑的喊了一聲:“巴帕。”接著急急地跑上幾部,雙手抓住馬勒,幾近哀求的說:“如果將來有了孩子,送過來,我養大了再還給你們!”眼睛裡一下子噙滿了淚水。
白音寶力格震驚的聽完這段的表白,目不轉睛的望著索米婭。
白音寶力格馳騁駿馬,飛馳草原。那一浪浪湧來的、蒼涼古樸的調子此刻也有意無意的叩擊著。在長調久久不散的餘音終於悄然逝盡的一刹那,滾鞍下馬,悄悄的流淚。
我也跟隨此情此景,在想:那個梳著羊犄角小辮和我同騎一牛的小女孩,那個緊束著腰帶朝我奔來的少女,那個紅霞中的姑娘,還有那個趕車人泥屋裡的四個孩子的母親,那個整天鑿冰做體力活的年輕婦人,居然都是一個人。光是歲月從中作梗,難以把這一切聯繫起來,我想這就是命運。我是一個有點宿命的人,因此相信,不管雙方如何努力,結果都是意料之外。
合上書後曾想:既能看到過去又能看到未來的索米婭該怎麼辦;已是大學生的白音寶力格能否容下一片空白格,放下過往,從頭再來。是否真的遇上真情人,生完孩子送來草原來,讓索米婭養大;其其格會不會忍受達瓦倉的謾駡,埋頭讀書終將走出去;黃毛鬼希拉又將因為這觀天的罪孽,躺在臭水溝裡,痛苦老去;甚至再想,索米婭和白音寶力格的孩子,未來能否續上上輩子的情緣。
反反復複看完幾遍之後,已經不再憐傷這段情的刻骨銘心和百轉千回,不再替小說的角色做一切妄想。小說的結局難以改動,而生活完全由自己做主。因此從空想的理想主義中抽離出來,踏踏實實的生活,坦然平靜的接受生活賦予的一切。畢竟,死亡的終點,每個人都在倒計時。
曾經看到品特的一段文字:我們在大多數時間裡都是沒有表現力的,不露真情,不可信賴,難以捉摸,含糊其辭,障礙重重,扭扭咧咧。在我看來,任何人都逃不開這猶猶豫豫而又停滯不前的心結,最重要的是否能夠帶著最初的那份感動和理解,繼續走下去。只是走的太遠,不要忘記我們當初為什麼要出發……
近段時間,周圍的同學和老友都曾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鄭重其事地告訴我:你真的變了一點。宿舍哥們說,我變得有點賤賤的,漸漸的加入了“很黃很暴力”俱樂部;不常見面的同學偶遇說,我開始像個成熟的人了,至少外表裝得蠻像。老友聚在一起說,以前覺得你像冰一樣,進不去。一旦熟識,就收不回來了。
不管對我的是調侃,還是“調戲”,我都能坦然的接受。近些年來,逐漸開始平實下來,沒有當初的冷對橫眉,也不會再獨享寂寞,既不在刻意在意所謂的面子,也不想附和著裝腔作勢。心結漸漸打開,人也變得稍許從容和平靜,周遭的不順和困境,也能適當的宣洩和放空。
或許,有時我們在抱怨,理想一代被現實紮破的體無完膚,控訴命運的不堪和冷酷,才發現一切都沒有離開過,只是我們的心境在悄悄的變質罷了。汪涵曾經說過一句話,無論你是日漸繁華,還是即將枯萎,此時此刻就是你的人生。
Copyright © 2002-2025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