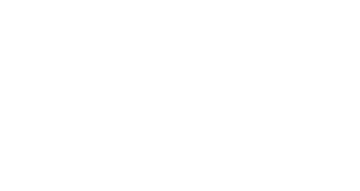塑膠袋,我把錢夾放了進去
塑膠袋,我把錢夾放了進去
塑膠袋,我把錢夾包裝袋放了進去。她把袋子交給了卡利特。
“如果你沒意見的話,我們將把這位先生的遺骸送到太平間去。盧梭小姐會確認他的身份並盡快通知他的親人藥袋。”
米勒看了看自己的表,我們也都下意識地擡起自己的手腕,像是巴甫洛夫的小狗。
“快七點了,”卡利特說,“今晚沒什麽事了。”
警長沖我和米勒點點頭,把墨鏡架回鼻梁,一聲口哨叫上自己的狗朝路邊走去。
趁同事們把樹上剩余的繩子剪斷裝進證物袋的工夫,米勒和我確認了一下現場沒有什麽地方還可以榨出情報來。我們站在那裏,只感覺到頭上藤蔓叢生,耳邊蚊子嗡嗡,旁邊黝黑的沼澤裏滿是爬蟲們的聒噪。
等到米勒終于關上驗屍部的面包車門時,天空顯現出一片南方沿海低地特有的血色黃昏。她臉上滿是蚊子叮的包,前胸後背一片汗濕。
“我待會兒就給愛瑪打個電話,”我說,“告訴她最新的情況。”
“謝了,寶貝。我腦子裏又省下一樁要記的雜事。”
我站在路邊撥號,鈴響了三次後愛瑪才接聽,聲音單薄尖厲。我跟她說了事情的過程。
“真不知該怎麽謝你。”
“客氣什麽啊。”我說。
“薩默菲爾德家可以松口氣了。”
“是啊。”我答應著,毫無激情。熟悉的場景,有人歡喜有人憂。
我聽見電話裏深吸了口氣,結果對方卻沒說話。
“什麽事?”
“已經夠麻煩你的了。”
“沒什麽的。”
“真不好意思再求你。”
“求我?”
置物櫃 停了一下,接著說:“我明天有個治療。我——”
“幾點?”
“約了七點。食品袋”
“那我六點半來接你。”
“太謝謝你了,唐普。”聽到她那滿懷感激的語氣,我眼淚都差點掉下來了。
我又帶著一身死亡的氣息回了家。一回家我還是沖到戶外淋浴棚裏,把水溫調到能承受的最高點,打上香皂和香波沖了一遍又一遍。
博伊德一如既往地熱情歡迎我,先是擡起前腳,然後又繞著我的腳轉“8”字圈。博迪不以爲然地、或許是輕蔑地看著它。貓的心思誰說得清。
我穿好衣服,裝滿了貓盆狗碗,然後查了一下電話。賴塑膠袋安沒打電話來,也沒給我的制服手機發短信。皮特的車沒在外面。除了貓和狗,房子裏空空的。
我一解開皮帶,博伊德就上躥下跳,在廚房裏不停地轉圈,最後前腳著地,尾巴豎起來,我只好帶它到沙灘上遛了一大圈。
回到家,我又檢查了兩部電話,還是什麽也沒有。
“給賴安打電話嗎?”我問博伊德。
小狗抖了抖眉毛,歪著腦袋看我。
“你是對的。如果他還是不高興,就給他一點個人空間。如果他忙,他過一會兒會打過來的。”
我上樓回到自己的夾鏈袋房間,敞開玻璃門,倒在了床上。
博伊德趴在地板上。我躺著,卻久久不能入睡,聽著海的聲音,聞著海的氣息。
不知什麽時候,博迪跳了上來,踡在我的身邊。迷迷糊糊之中我想到要吃東西。
卡利特說對了,那晚後來就沒什麽事了。
“平克尼?”
Copyright © 2002-2025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