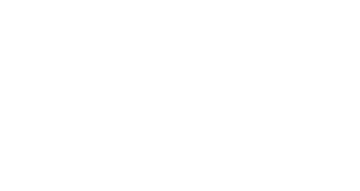18里的半夜雪路
大雪紛飛,看不見四周,只留下一條彎彎曲曲的雪路還在延伸著。
我戴了像雷鋒叔叔戴的那樣的棉帽子,帽激光脫毛檐下,兩片帽簾兒剛好護住耳朵。
腳上穿得特別時髦,我們叫它翻毛大頭鞋,走起來“吱嘎吱嘎”亂響,鞋底還黏了不少雪,一只起碼五斤重,小小的身子在茫茫曠野里一顛一簸地移動。汗Wall Garden冒著熱氣兒,把里層的衣裳都溻透了,棉襖的外頭罩了爹的黃布褂子,雪花落在褂子上化了,又迅速凍上,硬邦邦的,兩個胳膊一甩,“啪啪啪啪”響,好像一個小兵馬俑在走路。好在,寒冷滲不到身子里,滿肺腑都是火熱的,讓人渾身有勁兒,一點也不感到冷。
此刻,遠的村,近的樹,平坦的麥田,孤零零的麥稭垛,我看見大雪給眼前的世界蓋上了一層厚厚的棉花被子,萬事萬物都在被窩里,“呼呼——呼呼”,睡得好香啊!
想到這個比喻,我都有些羨慕它們了。我的胳膊呀腿兒呀,也不是我的了,凍得硬邦邦的,像光禿禿的小楊樹,站在土路兩邊。嘿,這麽冷的天,它們還站在那里,傻得不透氣了!可是,它們不站在路邊,應該站在哪里呢?
不知不覺,黃昏時從鎮中學出發,我已經走過了8個村莊,天完全黑下來了。天是白皚皚的,因下雪了,一直像大白天似的。可現實里,這還是在黑夜啊!人們都睡著了,雞鴨鵝牛羊馬都睡著了,鳥雀們睡著了,一個靜寂的世界里,只剩下大雪的“噗噗噗噗”聲,還有我“吱嘎吱嘎”的走路聲,再沒有別的什麽東西了。
剎那間,靜,一把抱住了我,緊緊地,好像一個許多年沒有見面卻想死了我的親戚,親熱得不得了,激動得說不出一句囫圇話。可惜,這種靜很巨大,很虛空,很冷,天地人神皆空,令我不寒而栗。
耳朵有些聽不見聲音了,我壯著膽子,“啊”了一下,根本沒有什麽回聲,雪下得太大了,雪花把天地之間的空氣都填滿了。
我摟住頭,揪了揪帽簾兒,又“啊”了一聲,這下子,我聽見自己的回聲了!雖然很短、很急促,但很真實,不虛空,否則,我就會無聲無息地被大雪吞噬了。
腳步慢了,身上的熱氣一絲一縷被北風抽走,開始還不怎麽察覺,等察覺到了,熱氣早散完了,只留下一身冷冰冰的外殼。我下意識地緊跑十幾步,果然,腳心開始出汗、發熱,但渾身依舊冷,小胳膊小腿很硬,伸不直,每個動作都顯得多余,冷啊,冷得整個牙幫子亂打寒戰。從北往南,走到高莊村的時候,我就想,要是碰見一個親戚多好!是親戚都親,會跟我打招呼啦,問候啦,讓我好一頓吃吃喝喝啦,哪怕安慰我幾句,不管是近門的,還是遠房的,都中!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走過了小蔣莊、大石營村,我連個麻雀也沒有碰見。天這麽冷,雪這麽大,別說是人了,連麻雀都知道鳥窩里暖和,你想想,誰還會在雪地里亂跑呢?
快到小石營村了。遠遠地,一個黑點向我移動,近了一點點看,是人,好一陣驚喜,啊,終於見到人了。
那是一個背麥稭兒的農民。一條黑頭巾纏在他的頭上,長長的,裹了幾個來回,露出兩只賊溜溜的眼睛,讓人認不出來、看不出年齡,好像是故意的。
我高興起來,跑代替了走,特別快樂,不管認不認識,想跑過去跟他打招呼。相反,那人走得緩慢,很遲疑,眼神有些躲躲閃閃,是不是他不想理我?
我迎了過去,他迎面走來,跟我擦肩而過,真快。隱隱約約之間,我聽見一個低沈的聲音說:“你是,建偉吧?”
我很奇怪,他怎麽知道我叫建偉,一下慌了神,忙問他:“我不認識你。你說說看,我是哪個村的?”
他說:“蔣寨的。我不光認識你,連你爹我也認識。”
沒等我再問,他轉身走了,也不多解釋,留下我站在原地,滿腦子的問號、逗號和省略號。哎呀,這個家夥,也不知道他算老幾,幹什麽的,竟然知道我的大名,嘿,有意思,真有意思。
18里的半夜雪路
走著走著,再一想,大雪天,他背了一筐麥稭兒幹什麽?臨近年關口上,難道他們家沒柴火燒了,沒辦法過年,他是一個偷麥稭兒的賊?關鍵是,他認識我,別人抓住他的話,那人會不會誣陷我也是小偷?如果那樣,會不會……我不敢往下想了。
突然,一種巨大的恐懼感襲來,天,一下子租務成交通到地上,就像一口巨大的鍋排子——就是奶奶拿秫稭莛子排的那種——直直地從頭頂罩下來,讓你來不及掙紮,就上西天取經去了。恐懼,絲絲縷縷地積攢,一層一層壓迫,讓你喘不過氣,無法正常呼吸。心,宛如一架中彈的飛機,想努力攀爬上升,卻總上不去,在雲層里越飛越低,踉踉蹌蹌,最後,一頭墜入谷底。
我只有一路小跑,大跑,再小跑大跑。淩亂的腳步聲,擠滿耳朵。
直到我上氣不接下氣地跑到蔣寨村,跑回家里,一口氣喝了兩大碗“茶”——也就是白開水,方才緩過神來,大叫一聲:“哎呀,我的娘啊!”然後,我跟爹、娘和姐姐他們好一番講述,也說起了那個賊。
聽完,我爹神色平淡,司空見慣地說:“大石營村的你二姑父家,地少,人多,他也常常去別的村子偷麥稭兒燒。”
二姐說:“呸呸,二姑父原新一代hifu來是個賊!”
我娘說:“說不定,那個人是你二姑父哩。”
我爹脖子一扭說:“你胡說個啥?咱親戚里咋會出賊?”
大姐說:“我猜,就是我二姑父。”
我爹打岔道:“再瞎說,我真拿一根針把你的嘴縫上……”
不想,大姐小嘴一撅,故意做了個傻乎乎的動作,惹得我們一陣亂笑。
其實,我和姐姐們好像一群小雞,鉆進父母巨大的翅膀下取暖,這才是世上最快樂的事情,誰是那個賊,已經沒什麽意義了。
我很佩服自己,12歲,3個小時,15個村子,小小激光脫毛的年齡,竟然從小鎮中學走回家,一口氣走了18里路。那,可是18里的半夜雪路啊!
Copyright © 2002-2024 all rights reserved.